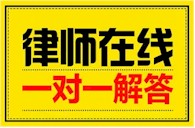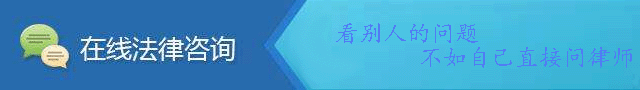一、我国刑事法中的孕妇,哺乳期妇女
(一)我国刑事法有关孕妇、哺乳期妇女的规定
孕妇,哺乳期妇女均属于特殊法律主体,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习惯称之为“两怀妇女”。⑴涉嫌刑事犯罪时,由于身份特殊,刑事法对其给予了特殊关照。其中,有关孕妇的规定较为明确,但关于哺乳期妇女,刑事法上并未采用这一概念,与之相关的,是有关“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取保候审。如果这一规定对两怀妇女的特殊关照体现得尚不够明显的话,以下各项规定则无疑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对符合逮捕条件,但有特殊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其中就包括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对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如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除此之外,还体现在专门针对孕妇的规定: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还规定,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停止执行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另外,有关司法解释也对孕妇的刑事法适用作了进一步明确。1983年9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对人工流产问题作出了答复: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前,被告人(孕妇)在关押期间被人工流产的;或者法院受理案件时,被告人(孕妇)被人工流产的,仍应视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⑵1983年12月3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二)》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含义加以了明确:不适用死刑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适用死缓。1991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如何理解“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在羁押期间已是孕妇的被告人,无论其怀孕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论其是否自然流产或者经人工流产以及流产后移送起诉或审判期间的长短,均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⑶1998年8月13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延续了上述立场,对自然流产问题进行了回应:“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
(二)对“孕妇”的刑事法解读
孕妇,顾名思义,即所谓怀孕的妇女,似无进一步解释的必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孕妇的规定,在法条中使用的就是“怀孕的妇女”等类似表述,此即为明证。然则,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明了,尤其是在针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的理解上,存在较多争议。
从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孕妇的理解,已远远超出其通常意义的范围。以我国《刑法》第49条的规定为例,若严格遵守其字面含义,不适用死刑的妇女仅限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即从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之日起,至法院作出最终裁判(含审判监督、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裁判)之日止,处于怀孕之中的妇女。然而,经由种种司法解释,审判前已经人工流产、自然流产的“曾经的孕妇”也被解释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并且,从《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的规定来看,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亦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发现“正在怀孕”,通常是指审判时已怀孕,因为种种原因,在审判时未能发现的情形,这仍在《刑法》第49条的调整范围内。然而,我们不能排除如下这种特殊情形:在审判时尚未怀孕,但在死刑交付过程中怀上身孕的。虽然这种情况通常难以发生,但无法排除理论上的可能,例如,被监管场所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男性强奸而怀孕;或者为活命而有意勾引男性,乘机怀上胎儿的;或者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得与丈夫同房的机会,并怀上胎儿;甚或人工授精;等等。尤其是在死缓执行期间,2年的缓刑考验期给女犯怀孕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空间与可能。显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怀孕,已无法解释为“审判的时候怀孕”。
对于上述无法纳入“审判的时候怀孕”的诸种情形,司法解释和《刑事诉讼法》第251条均排除死刑的适用,法律依据何在?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对“审判”一词作扩大解释,认为这里所说的“审判”不限于法院的审理裁判活动,还应包括为审判而进行准备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诉讼活动,以及为实现裁判而开展的刑罚执行活动。这实际上是将“审判”等同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这样的解释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为何刑法要选取“审判”一词以代表整个诉讼活动,而不直接表述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呢?尤其是《刑法》经过1997年修改之后,依然保留了1979《刑法》的原文表述,这是值得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的。扩大解释的结果是:《刑法》第49条所规定的“审判”与刑事法其他条文中的“审判”无法作统一的理解,从而一手“创设”了法律上的矛盾与冲突。
除了《刑法》第49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有关适用强制措施、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中也涉及孕妇。对《刑事诉讼法》中的孕妇一词,尚无相关司法解释。我们认为,为有效保障孕妇的合法权益,促进法律统一,应对孕妇一词作统一解释,将人工流产、自然流产后的妇女也解释为孕妇。
二、对孕妇、哺乳期妇女的刑事法保护
(一)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对孕妇、哺乳期妇女,一般应尽可能避免人身羁押。但就刑事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而言,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可否适用拘传?拘传实质上系一种强制传唤,不具有人身羁押性质,且属于所有刑事强制措施中强制程度最轻的一种,因而,对孕妇、哺乳期妇女适用拘传,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应予注意的是,即使是拘传,也有其适用条件和程序。对孕妇、哺乳期妇女进行拘传,更应严格依法实施。拘传的适用对象是经合法传唤拒不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不得未经传唤而径行拘传,拘传持续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24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即使存在经合法传唤拒不接受讯问的情形,也应尽可能避免采取拘传措施;即使适用拘传,也应时刻注意其身体状况,保障胎儿的安全或婴儿及时得到哺乳。
第二,可否适用拘留或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可以监视居住。在这里,除了特定身份的要求,不再附加任何其他适用条件。这表明,只要是孕妇、哺乳期妇女,一般应排除逮捕的适用。但法条中“可以监视居住”的表述表明,适用逮捕的可能依然存在。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逮捕,尚无明确的标准或条件。从审前羁押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保障诉讼、人权保障等其他价值的彰显,都是建立在肯定羁押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如何规范羁押措施,以消除负面影响。因此,对孕妇,哺乳期妇女适用逮捕,仅限于不予逮捕有较为明显的妨害诉讼、继续犯罪等现实可能。虽然有妨害诉讼、继续犯罪的可能,但若无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是迫切的、明显的,不得适用逮捕,否则,有可能导致上述规定流于形式,从而无法有效保障孕妇、哺乳期妇女的合法诉讼权益。
第三,可否在人工流产、自然流产后对孕妇适用逮捕?对孕妇,不能待其流产后适用死刑,这已有司法解释予以了明确,但对孕妇,可否在其流产后适用逮捕呢?对此尚无任何规定。我们认为,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一般应排除逮捕的适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基于胎儿的考虑,而且考虑了孕妇本身情况,不能因为胎儿的流产而不作人道主义考量。在现实中,有些侦查机关为了对孕妇适用逮捕,以强制手段迫使孕妇人工流产,这种做法实际是在恶意规避法律规定。法律是用来遵守、执行的,恶意规避法律规定,当然为法律所禁止。如果认可上述做法的法律效力,无异于鼓励侦查机关违法办案。
(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
暂予监外执行系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立法初衷是为了解决不适合在监管场所执行刑罚的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然而,由于对监外执行存在监管不力等问题,在某些地区甚至处于一种近乎无人监管的状态,包括保外就医在内的暂予监外执行差不多就意味着罪犯的提前释放。如此一来,暂予监外执行就成了自由刑人犯眼中人人欲得而食之的“唐僧肉”。为获得暂予监外执行,人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对于以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得暂予监外执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刑期。但是,以恶意规避法律的方式获得暂予监外执行的如何处理,法律未曾涉及,需要加以探讨。
对孕妇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虽然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暂予监外执行,但对孕妇不予监外执行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由于暂予监外执行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通过恶意怀孕的方式获得暂予监外执行就有了强劲的源动力。在上海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是为适例:一妇女因犯罪被刑事拘留后,采取欺骗手段被认定为孕妇,遂获得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成功怀孕,因而在刑罚执行时得以暂予监外执行。后来虽然查明骗得取保候审的证据,但取保候审期间怀孕却是事实。这位孕妇恶意怀孕的情形是较为明显的,对其可否暂予监外执行?
对哺乳期妇女暂予监外执行也存在具体适用问题。如前文所述,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若对其作事实的判断,则只要哺乳自己孩子的事实状态一直在持续,就可以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只要孩子一天不断奶,母亲就不会被收监执行。为了继续享受监外的自由生活,刑期中的母亲就会“将哺乳进行到底”,刑期不止,则哺乳不息。这样的情形,无疑是在恶意规避法律。实际上,学界、实务部门一些人士已对此有所关注,并呼吁对哺乳期作适当限制。⑺
对于恶意怀孕,我们认为应排除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原因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非“应当”,而是因为恶意规避法律不是对法律的遵守与执行,恰恰是对法律的破坏与背叛,是从根本上对法律进行否定,是对法律精神的反讽。承认它即是否认法律,保护它即是破坏法律,从而呈现出法律上的“悖论”。从一般法的意义出发,我们认为,恶意规避法律从来不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永远归于无效。对于“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应该限定为“哺乳期妇女”,应作法定身份的解读。对于哺乳已满1周岁儿童的妇女,一般应排除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排除适用的理由同样不在于法律规定上的“可以”,而在于恶意规避法律的无效性。
(三)适用死刑的排除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明确排除了死刑对孕妇的适用,且不存在例外适用死刑的情形,因而较好维护了孕妇的合法权益。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仍有具体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恶意规避死刑。恶意规避死刑属于恶意规避法律的一种情形。在一般法的意义上,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如果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坚持这一立场,就会得出对恶意规避者适用死刑的结论。因此,对恶意怀孕的孕妇,理论上就有了适用死刑的可能。但死刑适用显然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有刑事政策方面的考虑。尤其应予注意的是,当下的国际环境及今后的发展趋势是死刑的限制适用与废止。我国是尚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但慎用、少杀是我们一贯的坚持。从理论上来说,恶意规避法律的行为应当禁绝,但从刑事政策考虑,对恶意规避死刑的孕妇适用死刑面临巨大的舆论与道德压力。在保留死刑饱受争议、屡遭诟病的情势下,应该仔细权衡恶意规避法律与保障生存权之间的利弊得失。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罹罪之人不择手段,一心向生,系人性本能,其情可原,其心可悯。中华传统文化亦云:“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充分体现了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积淀。因此,我们认为,在废止死刑的立法趋势、刑事政策、人道主义精神及传统文化的合力作用之下,“恶意规避法律无效”的理论坚持有必要作出让步,放孕妇一条生路。
第二,有关孕妇是否适用死缓的思考。由于死缓系死刑执行方式之一种,并非独立的刑罚种类,对孕妇不适用死刑,当然意味着不得对其适用死缓,因而似无讨论的必要。但在我们看来,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轻重落差与实质差异,将死缓定位为死刑执行方式未必妥当。
死缓系我国死刑适用制度上的独创。究其原因,既有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也有在废止死刑的强烈吁求声中作折中处理的意味。但是这种独创未必“讨巧”:对罪犯适用死缓,在批评者眼中仍是在适用死刑,其效用却是“授人以柄”,在支持者看来,实际上已是放人一条生路,值得肯定,但为何要冠以死刑之“恶名”?在被害人一方看来,空有死刑之名,该死之人终究脱死活命,期待中的善恶有报依然落空,对法治理想未免心生怨怼,在犯罪人看来,侥幸逃得一死,方知即使在法律上被宣告为死刑犯,却仍有生还的希望,良善者当然心怀感激,悉心改造,邪恶冥顽之人则可能从此看轻法律,无视法律权威,难收洗心革面之效。
对于有死刑之名却无死刑之实的死缓制度,在本质上,它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存在着生与死的巨大差别,在刑罚的轻重程度上,虽然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无期徒刑之间提供了一种衔接和缓冲,但在死刑制度内部,在同一种刑罚方法之下,轻重程度差异太过明显,难以统一于同一刑种之中。因此,将它独立为一个刑罚种类,或者将其废止,都好过现在的制度设计。正因为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存在上述差异,在立法未作修改之前,对孕妇是否适用死缓就有了商讨的余地。死缓并不当即剥夺人的生命;在保留人命的同时,给了罪犯自我救赎的机会,是否自救完全取决于自己。当然,如果同时规定,对判处死缓的孕妇,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当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第三,死刑执行过程中的怀孕。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第251条隐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死刑执行过程中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判决作出后,即使是死刑立即执行,在实际交付执行前,中间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如果判处的是死缓,其间则有长达2年的考验期。因此,在死刑交付执行阶段,尤其是在死缓的执行过程中,犯罪妇女怀上身孕的可能就无法被排除。对于这种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1条的规定,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停止刑罚的执行;经查证属实的,应予改判,即不得适用死刑。从绝对排除对孕妇的死刑适用的立法本意来说,这样的结论是合适的。但问题是,刑事诉讼法系程序法,不得对是否适用死刑这类实体问题加以规定,而这种情形又不在《刑法》第49条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其合法性就有了疑问。
对孕妇绝对排除死刑的适用,这完全符合立法本意;对死刑执行过程中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是当然的结论。鉴于刑事诉讼法无权就刑罚适用的实体问题作出规定,我们建议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不适用死刑的情形写入《刑法》。
第四,哺乳期妇女是否不适用死刑?在我国刑事法中,哺乳期妇女只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与刑罚执行方式上获得关照,在死刑适用方面未获特殊照顾。因此,从立法规定来看,显然不可能排除死刑的适用。但从应然的角度观察,有无必要给予哺乳期妇女不适用死刑的关照?若严格限定1年的哺乳期,对哺乳期妇女不适用死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借鉴域外的经验,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如2年)内暂不执行死刑(指死刑立即执行),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五,宫外孕、葡萄胎等异常怀孕情形下的死刑排除适用,有学者对异常怀胎,尤其是胎儿无法存活情形下的死刑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提出,异常怀孕的妇女属于孕妇,即使胎儿无法存活,仍应排除死刑的适用。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不能因为异常怀胎而否认其孕妇身份。且如前所述,人道主义精神针对的不只是胎儿,还有孕妇;即使查明胎儿无法存活,仍有给予孕妇特殊关照的必要。
我国刑事法律负哺乳期的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就司法实践来说,哺乳期的时间为一年,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哺乳期犯罪的规定,若犯罪嫌疑人在哺乳期内实施犯罪行为,是可以执行监外执行的,这也是孕妇不适用死刑规定的体现。
⊙声明:本页内容仅代表发帖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同意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侵权或违法违规,请点此举报。
⊙相关内容
·敲诈勒索罪的量刑
一、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二千元,或两年内敲诈勒索次数达三次,在四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敲诈勒索公私财......
·法律上是怎样认定诈骗罪
诈骗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某人或某一团伙在取得别人的信任或者不自愿的要求下后,其行为已经对社会有重大消极影响。那么对于诈骗的行为,法律上有什么可参考的标准呢。遇到此类事件后,我们该怎样认定诈骗罪。怎样认定诈骗罪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客观方面包括哪些要件...
近几年来,有关非法传销活动的报道时常见诸于各大媒体,这些传销活动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分工明确,专门诱骗那些抱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的受害者,对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严重损害,作为非法传销的组织领导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上海运输毒品罪最新量刑标准
针对运输毒品的行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为犯罪,即运输毒品罪,此时就要按照相关规定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要是在上海犯此罪的话,具体该如何量刑处罚呢?我们提供上海运输毒品罪量刑标准的规定,帮助你进行了解。一、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幅度的量刑起点和......
·南京中小企业法律服务
南京中小企业法律服务律师为南京市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企业创......
 安徽 史微微律师 |
 部门主任 法学学士 部门主任 法学学士 |
 15955028395 1595502839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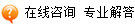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安徽 王庆磊律师 |
 副主任 法学学士 副主任 法学学士 |
 18056899334 1805689933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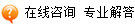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浙江 温.律师 |
 副主任律师 法学硕士 执业11年 副主任律师 法学硕士 执业11年 |
 13052261268 130522612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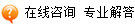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江苏 王奋永律师 |
 副主任律师 执业14年 副主任律师 执业14年 |
 13952106950 1395210695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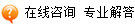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山东 许义园律师 |
 法学学士 执业7年 法学学士 执业7年 |
 13061416368 130614163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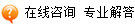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上海 唐敏峰律师 |
 执行主任 执业14年 执行主任 执业14年 |
 18501560386 1850156038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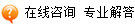 |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苏路178号邮政编......